
大家好,我最近研究了下民国时期的土匪。说实话,这段历史非常精彩。但看资料的过程很枯燥,各种生僻字也不好认。所以我不想把这种负担带给大家,准备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讲讲。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社会无序时期,而每逢乱世必出奇人,必生怪事。所以单拎出来就能讲的事情有很多,像施剑翘佛堂枪杀孙传芳,姜文《让子弹飞》开场的原型“临城劫车案”等。本身就属于民国奇案,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放在后面聊。

△ 姜文《让子弹飞》开场劫火车的画面来源于此
今天我想先讲点跟你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实用主义者总能在相对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得更好。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还是做生意,那些注重“行动”、“效果”的朋友可能都活得还不赖。
而论起这种生存能力,民国的匪首个个都是行家。他们不仅从事着绑架勒索,抢劫杀人的反社会活动,还摇摆在官,军、民、绅甚至外国势力之间,通过审时度势,闪转腾挪,帮助一方制衡另一方来不断获取利益。

可以说民国的匪帮既是恐怖主义的时代先锋,又是实用主义的真·实践派。我们知道实用主义的核心纽带是互利。所以在商品社会当下,实用主义实际上也已成为社会运转的基本法则之一。这听起来可能会有点不近人情,但现实情况却更加残酷。
好,闲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残酷的土匪世界。


1922年的一天晚上,一帮土匪在确信已经摆脱追兵之后,带着俘虏停下来休息,点火做饭。怀揣着对新“肉票”卖个好价钱的美好期待,大家互相传递着饭碗,一边盛饭一边把嬉笑声回响在小树林。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快跑!”原来官兵趁着匪徒围拢休息的机会,已经悄悄地摸上来,包围了他们:
土匪来不及把帐篷从木桩上拔掉。俘虏抓起跟前的东西拔脚就跑,负责看守的跟在后面急追。一个还处在大脑一片空白的小土匪,被推着急速往山下跑,好容易才抓住自己的羊皮外套没有掉。而匪帮其他东西包括小米步枪等,有一半都被官兵抢了去。


摆在土匪面前唯一的逃跑路线是穿过咆哮湍急的水流,它正好可以挡住追兵的来路。这时天上下起了寒冷的滂沱大雨。在近腰深的水里跋涉数小时后,所有的土匪都筋疲力竭,处在精神和体力双重崩溃的边缘:
一个土匪流着眼泪赌咒发誓,如果能够活着逃脱出去,今生今世再也不干土匪了!
而就在前几天,刚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一群土匪试图穿过河流逃避官兵时,他们的船不幸被冲上一处泥滩搁浅了,于是被迫在那里待了一整夜,头顶着倾盆大雨,双脚淹没在河水中。
漫长的雨夜,骨头被针扎般的湿冷,再加上看似无望,无法把握的处境,对这几个土匪的心理来说实在是太她娘的沉重了。
大雨滂沱中,几个土匪可能想起了一直来为吃口饱饭付出的艰辛,也可能想起因为没有地被当作农村边缘人口的歧视,娶不上媳妇,就连下决心当土匪后竟也发现跟自己的浪漫想象完全不一样……几个凶残的大老爷们,伴随着下雨打雷声,竟像个孩子一样委屈地大哭起来。

△ 哎呀,再也不敢做土匪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安全地过河,脱险之后,他们又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做土匪。
事实上,这才是民国百分之99以上土匪真实过着的生活。平均水平不如有地的农民,却要承担今日不知明日事,生死无常的代价。

△ 土匪吃口饱饭不容易
这样高压的精神生活,几乎决定了土匪近乎变态的消费观念。他们一有钱就会跑到距离匪帮最近的城里,吃喝嫖赌,把所有钱花光。这样的行为习惯被官军熟知后,有相当一部分侥幸活下来的土匪又死在了去花自己拿命搏来的钱的路上。
另外,疾病也是土匪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尤其是梅毒、淋病、沙眼以及过量抽鸦片所造成的胃病。其中鸦片被土匪当作治疗所有病痛的灵丹妙药,它既是一种有效的止痛药,又是一种能使人在短时间内迸发能量的无价之宝。在日常生活中,鸦片似乎满足了土匪的一切需求,经常可以代替食物、睡眠和娱乐。假如鸦片断顿,匪帮会变得极度焦虑惶恐。
因此有经验的人家,会在送给俘虏的包裹里塞进鸦片,以期在谈判中安抚讨好土匪;鸦片本身也常被当作赎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凶险的生存环境直接催生出暴力。在匪帮中,暴力和残忍是家常便饭。比如把孩子一撕两半,或者放在石滚子下面当长辈面活活碾死;用石膏封住眼睛;往鼻孔里灌煤油或醋;捆住俘虏的大拇指吊起来拷打;强迫长时间站在火堆旁边直到皮开肉绽等。听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由于投降或被擒之后的惩罚非常严厉,很多时候会像亮剑中黑云寨的二当家一样,脑袋被李云龙活劈下挂到城门楼子上去,因此土匪一般都顽抗到底。他们害怕被抓获被杀,无法摆脱对这种恶性循环的怨恨。恐惧和怨恨二者组成了各地土匪残酷行为的心理基础。

总结下来,你要是想在民国做一个土匪的话,必须要承受惊恐和朝不保夕,承受东奔西藏和不得安宁;承受悲喜无常,随时死于饥饿或暴食。
是完全抛弃人类社会,同时被人类社会所抛弃;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又不想和这个世界共存。简言之,过完全违背人类共处原则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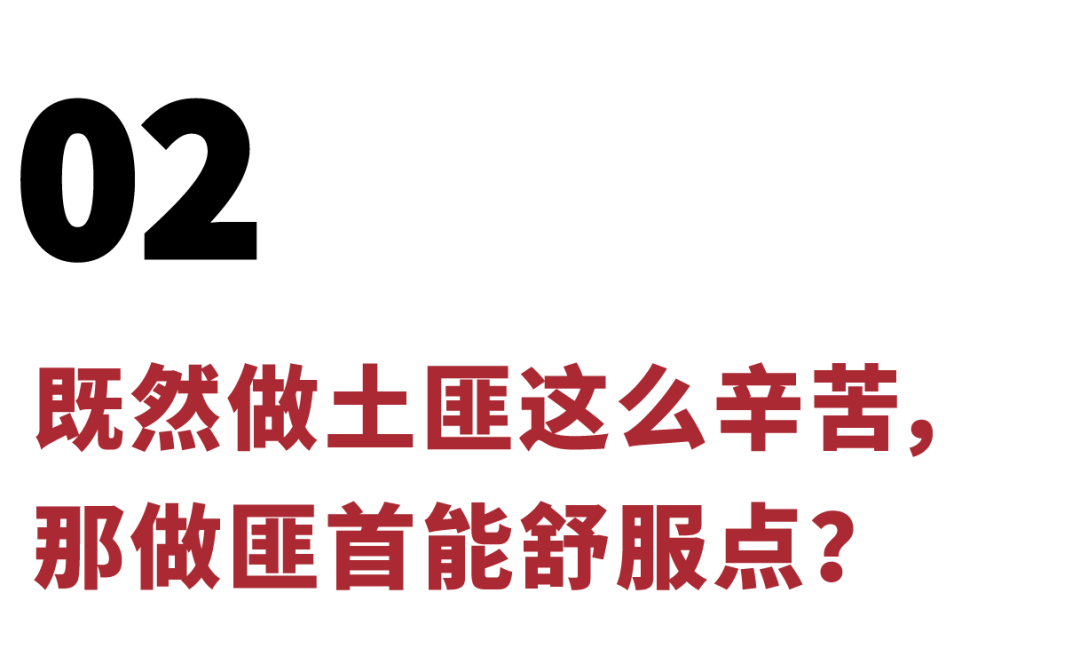
残酷的是,并不能。在任何地方,背叛对土匪头目来说都是一种日常威胁。
有明显迹象表明,河南第一大悍匪绰号“白狼”的白朗是被小头目杀死的,“老洋人”也是被以前的小头目所杀。指挥“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在临城谈判进入微妙阶段时,独自带领俘虏躲进一个孤立的山头,不和其他头目待在一起。而民国土匪中最牛逼的“东北王”张作霖,每晚睡觉都要更换地点,或者选派贴身保镖守护,这些保镖通常都是自己信得过的同乡。

△ 孙美瑶

作为土匪首领,你必须设法使部下对自己又敬又怕,同时还要对部下的情绪有足够的敏感,但你又不能过于敏感,以致显得虚弱。可以说,土匪头目是无一日不“如履薄冰。”
正如西西里匪酋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感慨:
我能够防范我的敌人,但只有上帝才能保佑我不受朋友的陷害。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土匪联盟的基本性质非常功利。对这些亡命徒来说,不法生涯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像电视剧中那种为革命组织随时献身的精神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极端的自私自利是每一个土匪的特点。
头目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但是这里专权并不意味着专政,土匪的组织特点决定了首领无法脱离部下。一个受人尊敬的首领,也得动不动忍受许多对他作为首领名誉含沙射影的攻击。
可以说是相当难受。
匪首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大类:一是“恶霸型”,二是“阴谋家型”。在民国动荡的环境中,前者有时倒也能出人头地,比如喜欢写打油诗的张宗昌可为代表。然而更典型的当推他的上司张作霖。

张作霖,身材瘦小,看上去非常纤弱,留着八字胡,是个文盲却文质彬彬。1904年,当他还是个南满的土匪首领时,日本军官就对他“外表如女人般文静,谈吐和风度却豪放直率”的印象深刻。1907年,张作霖把对他最有威胁的一个对手和对手的整个卫队请去赴宴,然后统统把他们干掉。


△ 张作霖最喜欢别人喊自己张大帅
在同时代的人中,张被看作具有天赋非凡的领导才能,既有开拓的勇气,又有灵活的外交手腕;非常善于捕捉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谈,什么时候该集中精力搞建设。
他天性机敏,具有政治和军事经验,很早便习惯于担当领导角色而获得了天然信心。可即使这样,1928年6月4日,行踪鬼魅的张作霖还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便撒手西还。其他如孙美瑶,白朗、“老洋人”这种领导几千几万人的匪首,从决定反叛政府那天起,离生命倒计时不超过5年。
可见,再厉害的匪首日子也不好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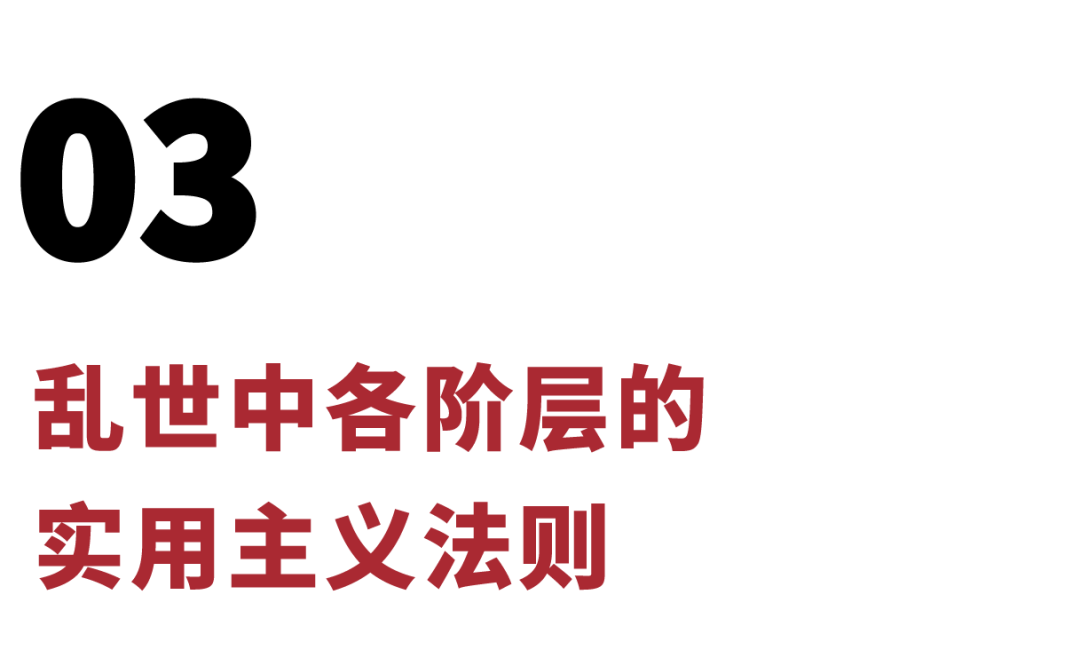
看过电影《教父》的朋友一定记得这一幕,老教父维克多被五大家族开枪打成半死后,有人告诉桑提诺:
It’s a business,not personal.
是的,虽然土匪干的是打打杀杀的活,但对他们来说这首先是一门生意。和你整天坐在办公室小隔间里哼哧哼哧做PPT一样,为的是挣钱吃饭,期待有一天发财致富!
尤其这么一份艰苦又危险的职业,要是还没把搏命赚来的钱花出去就被杀死,就太没意思了。所以除了极少数真正的“社会土匪”,摆出与地方权力机构毫不妥协的傻缺态度外,其他更多土匪是讲求实际的。他们本能地知道,要实现任何使他们激动的梦想的必由之路,是向任何一个愿意坐下来谈谈的人物妥协。

而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看,一般官员都把个人发财作为当官的主要指导思想。当官发财这点,《让子弹飞》里讲得最明白,电影中官绅勾结,借剿匪集资分钱的暗箱操作也属常规操作。到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才会拘捕几个土匪首领(如果他们能够抓到),抓不到首领就随便抓几个土匪冒充首领,脑袋砍下来写份向上的报告。报告里土匪活动的规模和人数会被大幅缩小,同时显示出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事给办了。轻轻松松,记小功一件。


△ 口号只是用来喊的
另一方面,从军事角度来说,县长能够差遣的不过几百人,而且是训练很少,装备很差的队伍。真要是动起手来,还真人五人六不起来。
军队倒是可以拉出来爆锤组织松散的土匪,但是不划算,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打仗太费钱了。不到万不得已,政府舍不得为土匪花。而普通军官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巧妙操纵“各种关系”,不断升官发财。士兵则是冲着军队提供的经济保障而来。打仗本身,对谁来说都是件毫无乐趣的事。
乡绅们愿意忍受土匪的原因也很好理解,以“临城劫车案”为例,军队在当地驻守仅仅两个星期,这个地方就陷于极度的困境,当地经济很快就没有能力承受驻军的负担。地方代表激动地表示,既然土匪如此真诚地想加入你们军队,就赶紧答应了人家啊,这符合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利益。
兵比匪凶,是也。
看吧,这乱世中没有一种关系能逃脱出利益相关,大家彼此利用又互不信任,在动态平衡中谋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无论你轻信了谁都有可能马上丧命。土匪正是机敏地利用这一点,作为讨价还价的有力工具。
在19世纪的多次反叛中,许多大匪一会投向政府,一会儿又投向反叛阵营,这种反复全视战争的命运而定。最厉害的匪首永远是实用主义的坚定践行者,他们懂得仔细观察风向,善于见貌变色,必要时从不会因为重操旧业而感到害怕或羞愧。事实上,他们生命的长度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精明程度。
比如豫西一位势力颇大的匪首张菊娃,以张寡妇的称号闻名。她先是为政府作战打当地的军阀部队,结果没打过被解除了武装。后又招募新兵,恢复元气后再次加入政府军。后出于敏感的嗅觉,她带领大家反叛做回了土匪。随后试图加入贺龙在四川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最终被河南剿匪司令刘镇华捕获,1931年被处死。
另一位从豫西崛起的农民领袖樊钟秀,更有万花筒般的职业生涯。
他首次应招去广州,对抗当地军阀,接着又应孙中山要求回河南,准备对付北京讨伐。讨伐失败后,他一会为冯玉祥反对阎锡山,一会又充当急先锋帮吴佩孚回去干冯玉祥。这期间自己也没闲着,还抽空到山里当了几次匪。之后冯玉祥准备去东北大干张作霖时,他又想趁机攻占洛阳和郑州。结果被冯玉祥精锐打垮了,这哥们再次转入地下。后来冯玉祥可能实在是折腾烦了,主动提出收编这群泥腿子。1930年夏天,这哥们终于在攻打许昌的战斗中被飞机炸死,结束了朋克的一生。
我们纵观民国土匪的众生相,虽然肆无忌惮、目中无人,却也命运多艰、惶恐不安。在无序社会中各阶层为利益展开的残忍斗争,直如恶鬼相扑杀,是一片人间修罗场的惨象。
怎么样,朋友,看到这里是不是再也不敢幻想梦回三国立下点不世伟业了?没关系,不要气馁,这世界本来就是凡人多,这种活还是留给那些天生的冒险家吧。
参 考 资 料:
《民国时期的土匪》,贝思飞,2010
《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何西亚
《绿林物语:土匪生活的一断面》 上田荣一
《红胡子的生活观》 孤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